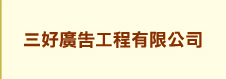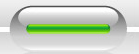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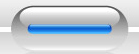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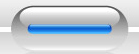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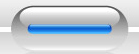 |
||
| 首 頁 | 關於我們 | 產品展示 | 聯絡我們 |

記者描述震后日本:災民一絲不茍過災區生活
系列深讀報道?
◆后來有人問我們是否想過核輻射的問題,實際的情況是,根本來不及想就進了福島,也來不及想就沖過去了。
◆幸運的是,早晨三四點,我們終于買到了幾小瓶茶飲,在災區30多個小時的飲用水就全靠它們了。
◆過慣富足生活的日本人并沒有“嬌氣”,他們忍受著種種惡劣條件,有條不紊地排隊,一絲不茍地過著災區生活。
◆就是在那時,司機告訴我們,從東京回國最早的機票是20日,那幾天票價被炒到20萬日元,幸好報社幫忙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□南方日報記者 張勝波
趙洪杰 王輝
在30多個小時里,沿著日本沿海突進災區,南方日報3名特派記者與地震、海嘯打了一個結結實實的照面。有險情,有難處,有悲傷,有鎮定,震后的日本至今記憶猶新。
通知標明張貼時間
日本9.0級大地震海嘯發生第31個小時后,南方日報特派記者就“空降”日本名古屋。第二天,我們到達距離東京最近的千葉縣災區。
小城浦安是東京迪士尼所在地,地震打破了這里的美麗和寧靜。一塵不染的路面滿是污泥,這是海嘯引發海水倒灌的結果;有些建筑物被整體抬高,原來的平地上陡然出現了“臺階”;水、電、氣停止供應,生活陷入混亂。
但是,自衛隊很快送來了飲用水,市政工人緊張搶修管道。當地居民歐陽先生說,這不全是政府下命令的結果,比如市政公司會覺得第一時間修繕管道是理所應當的,這更像是一種責任,而不只是救災。
與老師一道,家長的身影也出現在小學和幼兒園。地震發生后,學校給每位家長發了郵件,招募志愿者,幫助學校盡快復課。一名日本家長說,自己覺得這是作為家長的責任。
像是一架精確的機器,政府關于救災的指令清晰準確地發布著。在學校等公共場所,政府通告整齊地張貼在一起,通知什么時候供給飲用水,什么時候修繕哪條道路,什么時候預計可以通氣,救災信息在哪里可以查詢,等等。每一張通知,都清楚地寫上了張貼時間,精確到分鐘。
封路的消息不斷傳來
當天傍晚,我們才輾轉租到汽車,當時已經無人愿意去災區,在當地僑領的幫助下,我們才說服了兩位華人導游,他們答應“能走多遠走多遠”。
一路向北進發,汽車電臺上關于封路、斷路的消息不斷傳來,我們焦慮著:能否到達災區?
實際的困難還更多。還未駛離千葉,吃喝就給了我們當頭一棒。本打算買些飲用水應急,我們沖進超市才發現,只有幾瓶“依云”牌礦泉水“碩果僅存”,每瓶標價達數十元人民幣。我們嫌貴沒買,但很快就后悔了。整個晚上,我們幾次在路邊停車,但毫無例外地失望而歸——— 貨架冷清,清水、速食食品全部售罄,只剩下一些做飯的食材。店員也只能頻頻搖頭。
晚上10點半,我們終于找到一家旅館。房間已經住滿,但好心的店主允許我們在大廳寫稿,并用旅館的網絡發稿。在饑腸轆轆中,我們從災區發回了第一天的稿件。聽說我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,店員追上來送給我們一袋面包,他說:“很不好意思沒有地方住,送些面包算是表達歉意。”
不能住下,我們索性星夜兼程。到了茨城,道路破壞得更加嚴重,一些車輛呼嘯著撤出,我們孤獨地向前沖,偶爾有救災的車輛與我們并肩。地震已經讓這條“國道”破損不堪,隨時都可能出現交通意外。兩個司機不敢睡覺,一個開車,一個在說話幫駕駛員解困。搖擺中一夜無眠,我們3個記者也不敢睡。
高速不能走,大部分道路也已經封閉,我們只能曲折繞道。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,當地政府的交通管制有條不紊,道路一旦封閉,車載GPS就會在相應的道路上打叉,提醒市民不要再繼續前往,因此我們幾乎沒有見到交通擁堵的情況。
駛入日立公司所在的日立市,道路陷入漆黑。從這里開始,停電就司空見慣了。沒水沒電,旅館、餐館也都關門大吉,只剩下招牌燈箱在閃爍,吃飯的夢想遙不可及。
困難隨時都可能在身邊伏擊,讓我們無法抵達災區。我們說,這簡直是一場突擊戰,只有一往無前才有可能取勝。由于我們走的是海邊,距離福島出事的核電站不遠,后來有人問我們是否想過核輻射的問題。實際的情況是,根本來不及想就進入福島了,也來不及想就沖過去了。
幸運的是,凌晨三四點,我們終于買到了幾小瓶茶飲,在災區30多個小時的飲用水就全靠它們了。
一邊采訪一邊找飯店
緊繃神經,夜行百里。14日清晨,滿目瘡痍的仙臺機場映入眼簾。作為北部交通重鎮,仙臺受災沉重打擊了日本的北部交通,飛機一頭扎在地上的情形已經世界知名。
這是一個殘破的世界。翻滾的汽車堆積在一起,漁船上岸,房子殘破猶存,唯一通暢的就是一條剛清理出來的3米寬的路,可供汽車行駛。后來才知道,這是幸存的人清理出來的,供救援的車輛進出。
一些日本人已經從住所走出來,在機場附近尋找還能利用的物資,比如汽油。
在仙臺市區,“限量”成為人們生活的一個關鍵詞:便利店限量限時營業,大多數時候是掛著“暫停營業”的招牌,人們排起長隊,僅僅是為了一點兒臨時上架的瓶裝水;汽油每人限量20公升,每個加油站前都排滿了長龍,長期在東京生活的司機徐先生從沒見過這種情況,竟誤以為是在堵車;人們算計著吃飯。華人孫小姐每天早上只吃一根香蕉,中午吃幾片餅干,晚上基本差不多……
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,過慣富足生活的日本人并沒有“嬌氣”,他們忍受著種種惡劣條件,有條不紊地排隊,一絲不茍地過著災區生活。
已經連續24個小時沒吃飯的我們,一邊采訪一邊找吃飯的地方,但幾乎尋遍仙臺無果。中午快1點的時候,奇跡出現了:一家拉面店里傳來吆喝的聲音,店員正在忙活著開火。在災區的30多個小時里,這是我們吃的唯一一頓飯,已經非常“奢侈”。
教授寬慰留學生
地震發生后,很多人涌向了仙臺市的各個避難所,在那里尋找片刻的安寧,但那里的條件同樣艱苦。
見到我們時,正在東北大學留學的覃同學還沒回過家,一直住在學校附近的小學避難所。他描述說,避難所里幾百個人擠在一起,人們圍坐在電爐前取暖,這樣集體生活的情景他已經多年沒有經歷過了。但避難所每天只提供一瓢水和幾個飯團,從地震發生開始,他一直沒有洗過臉和手,更談不上洗澡。
這樣的避難所在日本災區超過2480多個,收容難民45萬多人。據了解,日本北部在此次地震和海嘯中損失了2.4萬棟房子,超過百萬戶家庭斷水、斷電,部分也沒有煤氣,很多人只能到避難所尋求幫助。雖然條件不佳,但失去家園的人們總算有個棲身之所。
作為這次災區采訪的一抹亮色,我們在仙臺幸運地看到了魯迅先生故居,它居然毫發未傷。
一個細節令人難忘。在東北大學(仙臺醫專被合并在這里),兩個華人留學生拖著行李,神情焦急,核輻射的陰影從恐怖的爆炸現場和國內親朋電話中傳來,但他們的一位日本教授面目沉著,教授寬慰說:“請不要緊張,相信日本政府。”
與海嘯擦肩而過
在仙臺市區,如果沒有超市和加油站門口長長的隊伍,我們根本發覺不了這里發生過重大災難,建筑物完好如初,在9.0級地震后沒有太大變化。整個城市整潔有序,地上沒有任何垃圾,也沒有混亂和哄搶的場景。
東北大學留學生小江經歷了特大地震,他租住的房子左右搖晃20多分鐘,嚇得他躲進了衛生間,但手機上很快顯示出仙臺市避難場所在哪里,哪條道路被封鎖也很清楚。
下午,我們繼續往北,準備去損失慘重的若林區看看。剛剛走上田間小路,迎面就停著一輛吉普車,一名男記者手持東方衛視的話筒在現場錄制新聞。我們打算跟他聊聊,找點兒線索,但一聊卻知道了或許是救命的“料”。
他告訴我們,同事剛剛從廣播上聽說,5分鐘之后海嘯將再次襲擊這里,大家趕緊撤離到離海岸遠一點的地方。不遠處,尋找了兩三百具尸體的警察也正在后撤。
我們幸運地避開了海嘯,雖然海嘯規模不大。
此時,關于福島核泄漏的消息越來越多,3號機組爆炸,形勢越來越嚴峻。司機緊張地說,往北走的話,我們的汽油不夠,不知道能撐多久,肯定沒辦法回來。他們堅決不肯再走。
無奈之下,我們只能沿著日本中部路線返回東京,尋找再次進入災區的機會。15日,我們接到了報社的撤離通知。就是在那時,司機告訴我們,從東京回國最早的機票是20日,那幾天票價被炒到20萬日元,幸好報社幫忙解決了這一問題。
相關閱讀:瘦肉精沖擊波 雙匯專賣店“易幟”